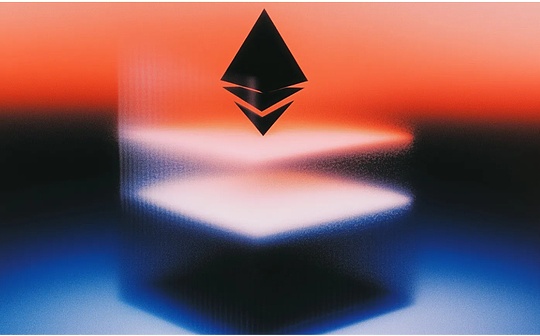來源:劉紅林律師
原來我根本不理解電
「五一」假期,自駕穿越河西走廊,從武威到張掖、酒泉,再到敦煌。開在戈壁公路上,公路兩旁時常出現一片片風力發電機,靜默佇立在戈壁之上,甚是壯觀,仿佛一條科幻感十足的長城。

*圖源自網絡
千年之前的長城,守的是邊疆與領土,而今天,這些風機和光伏陣列所守衛的,是一個國家的能源安全,是下一代工業體系的命脈。陽光和風從未像今天這樣,被如此系統地組織起來、嵌入國家戰略、成為主權能力的一部分。
在Web3行業,大家都知道挖礦是一個再基礎不過的存在,是這個生態最原始、也最堅固的基礎設施之一。每一輪牛熊切換、每一次鏈上繁榮背後,都少不了礦機持續運轉的聲音。而我們每次談起挖礦,談得最多的就是礦機的性能和電價——挖礦能不能賺錢、電價高不高、哪裡能找到低成本的電。
然而在看到這綿延千裡的電力之路,我卻忽然發現自己根本不理解電: 它從哪發出來?誰能來發電?它如何從大漠傳送到千裡之外,誰來使用,又該如何來定價?
這是我的認知空白,或許也會有夥伴對這些問題同樣充滿好奇。所以,我打算借這篇文章,做一點系統性的補課,從中國的發電機制、電網結構、電力交易、再到終端準入機制,重新理解一度電。
當然,這是紅林律師第一次接觸這個完全陌生的話題和行業,必然存在不足和疏漏之處,也請夥伴們多提寶貴意見。
中國到底有多少電?
我們先來看看一個宏觀事實:根據國家能源局在2025年第一季度公布的數據,2024年全年中國發電量達到 9.4181萬億千瓦時 , 同比增長4.6%,約佔全球發電量的三分之一。這是一個什麼概念?整個歐盟加起來的年發電量也不到中國的七成。這意味著,不僅我們有電,而且我們正處於「電力過剩」和「結構重構」的雙重狀態。
中國不僅發電多,發電的方式也變了。
截至2024年底,全國總裝機容量達到35.3億千瓦,同比增長14.6% ,其中清潔能源佔比進一步提升。光伏新增裝機約 1.4億千瓦 ,風電新增 7700萬千瓦。 從比例來看,2024年中國光伏新增裝機量佔全球52%,風電新增裝機量佔全球41%,在全球清潔能源版圖上,中國幾乎是一個「統治性角色」。
這種增長不再僅僅集中在傳統能源強省,而是逐漸向西北部傾斜。甘肅、新疆、寧夏、青海等省份成為「新能源大省」,正在逐步從「資源輸出地」向「能源生產主力」轉型。為了支撐這一轉型,中國在「沙戈荒」地區部署了國家級新能源基地計劃: 在沙漠、戈壁、荒漠區域集中布局超過4億千瓦風電和光伏裝機, 其中首批約1.2億千瓦已納入「十四五」專項規劃。

*亞洲第一座,敦煌首航節能100兆瓦熔鹽塔式光熱發電站(圖源自網絡)
與此同時,傳統的煤電並未完全退出,而是逐漸向調峰型、靈活型電源轉化。國家能源局數據顯示,2024年全國煤電裝機容量同比增長不到2%,而光伏和風電的增長率分別達到37%和21%。這意味著「以煤為基、以綠為主」的格局正在形成。
從空間結構上看,2024年全國能源電力供需總體平衡,但地區結構性過剩依然存在,特別是西北地區部分時段出現「電多用不了」的局面,這也為後文我們討論「比特幣挖礦是否是電力冗餘的出口方式」提供了現實背景。
一句話總結就是: 中國現在不缺電,缺的是「能調的電」「能消納的電」和「能賺錢的電」。
電誰能發?
在中國,發電不是一個你想幹就能幹的事情,它不屬於一個純市場化的行業,更像是一個有政策入口、有監管天花板的「特許經營」。
根據《電力業務許可證管理規定》,所有想要從事發電業務的單位,都必須取得《電力業務許可證(發電類)》,審批主體通常是國家能源局或者其派出機構,視項目體量、區域和技術類型而定,它的申請過程往往涉及多個交叉評估:
-
是否符合國家和地方的能源發展規劃?
-
是否已取得土地使用、環評和水保批覆?
-
是否具備電網接入條件和消納空間?
-
是否技術合規、資金到位、安全可靠?
這意味著,在「能發電」這件事上,行政權力、能源結構和市場效率三者是同時參與博弈的。
目前,中國發電主體大致分為三類:
第一類,是五大發電集團: 國家能源集團、華能集團、大唐集團、華電集團、國家電投。這些企業掌握了全國超過60%的集中式火電資源,也在新能源領域積極布局。例如,國家能源集團2024年新增風電裝機超1100萬千瓦,在行業內保持領先。
第二類,是地方國資企業: 如三峽新能源、京能電力、陝西投資集團。這類企業往往與地方政府綁定,在地方電力布局中佔據重要角色,同時承擔一定的「政策性任務」。
第三類,是民營及混合所有制企業: 典型代表如隆基綠能、陽光電源、通威股份、天合光能等。這些企業在光伏製造、儲能集成、分布式發電等板塊展現出強勁競爭力,也在一些省份拿到了「指標優先權」。
但即便你是頭部新能源企業,也不意味著發電廠你「想建就建」。這裡的卡點通常出現在三個方面:
1. 項目指標
發電項目需要納入地方能源發展年度計劃,必須獲得風光項目指標。這個指標的分配,本質上是一種地方資源控制——你沒有地方發改委、能源局的同意,就不可能合法啟動項目。部分地區還採用「競爭性配置」方式,根據土地節約程度、設備效率、儲能配置、資金來源等打分擇優。
2. 電網接入
項目批下來之後,還得向國家電網或南方電網申請接入系統評估。如果當地變電站容量已滿,或者沒有輸電通道,那你建出來的項目也沒用。特別是在西北等新能源集中的區域,接入難、調度難是常態。
3. 消納能力
就算項目批了、線路也有,如果當地負荷不夠、跨區通道沒打通,你的電也可能「無人可用」。這就出現了「棄風棄光」問題。國家能源局在2024年通報中指出,個別地市甚至因為集中上項目、遠超負荷,而被暫停新增新能源項目接入。
所以,「能不能發電」,不僅僅是企業的能力問題,更是政策指標、電網物理結構與市場預期共同決定的結果。在這種背景下,一部分企業開始轉向「分布式光伏」「園區自供電」「工商業儲能耦合」等新模式,以規避集中式審批和消納瓶頸。
從行業實務看,這種「政策準入+工程門檻+調度協商」三層結構,決定了中國發電行業依然屬於「結構性準入市場」,它並不天然排斥民營資本,但它也很難允許純市場驅動。
電怎麼運輸?
在能源領域,有一個廣為流傳的「電力悖論」:資源在西部,用電在東部;電發出來了,卻送不過去。
這是中國能源結構的典型問題:西北有豐富的太陽和風,但人口密度低、工業負荷小;東部經濟發達、耗電量大,但本地可開發的新能源資源非常有限。
那怎麼辦?答案是:建設 特高壓輸電(UHV) ,用「電力高速公路」把西部的風光電輸送到東部去。

截至2024年底,中國已投運的特高壓線路達 38條,其中交流線路18條,直流線路20條。 這其中的直流輸電項目尤為關鍵,因為它可以在極遠距離下實現低損耗、大容量的定向輸送。例如:
-
「青海—河南」±800kV直流線: 長達1587公裡,把青海柴達木盆地的光伏基地送電至中原城市群;
-
「昌吉—古泉」±1100kV直流線: 長達3293公裡,創下全球輸電距離和電壓等級雙紀錄;
-
「陝北—武漢」±800kV直流線: 服務陝北能源基地與華中工業腹地,年輸電能力超660億千瓦時。
每條特高壓線路都是一個「國家級項目」,由國家發改委、能源局統一立項,國家電網或南方電網負責投資與建設。這些項目投資動輒數百億元,動工周期2—4年,往往還需要跨省協調、環保評估和落地安徵遷配合。
那為什麼要搞特高壓?其實背後是一個資源再分配的問題:
1. 空間資源再分配
中國的風光資源和人口、工業嚴重錯位。如果不能通過高效輸電打通空間差異,所有「西電東送」的口號都是空談。特高壓就是用「輸電能力」去置換「資源稟賦」。
2. 電價平衡機制
由於資源端和消費端的電價結構差異大,特高壓輸電也成為實現區域電價差調節的工具。中東部可以獲得相對低價綠電,西部可以實現能源變現收益。
3. 促進新能源消納
沒有輸電通道,西北地區很容易出現「電多用不了」的棄風棄光局面。2020年前後,甘肅、青海、新疆的棄電率一度超過20%。特高壓建成後,這些數字已下降到3%以內,這背後正是輸電能力提升帶來的結構性緩解。
國家層面已明確,特高壓不只是技術問題,更是國家能源安全戰略的重要支柱。未來五年,中國還將繼續布局「十四五電力發展規劃」中的數十條特高壓線路,包括內蒙古至京津冀、寧夏至長三角等重點工程,進一步實現「全國一張網」的統一調度目標。
不過需要注意的是,特高壓雖好,也有兩個長期爭議點:
-
投入高、回收慢: 一條±800kV直流線投資往往超過200億元,回本周期超過10年;
-
跨省協調難: 特高壓需穿越多個行政區,對地方政府之間的協同機制提出高要求。
這兩個問題,決定了UHV仍然是「國家工程」,而不是企業自由決策下的市場基礎設施。但不可否認的是,在新能源迅速膨脹、地區結構錯配加劇的背景下,特高壓已經不是「可選項」,而是「中國版能源網際網路」的必選項。
電怎麼賣?
發完電、送出電,接下來就是最核心的問題: 怎麼賣電?誰來買?多少錢一度?
這也是決定一個發電項目是否盈利的核心環節。在傳統的計劃經濟體系中,這個問題非常簡單:電廠發電 → 賣給國家電網 → 國家電網統一調度 → 用戶交電費,一切按國家定價。
但這個模型在新能源大規模併網之後,已經完全跑不通了。光伏、風電的邊際成本接近於零,但其出力具有波動性和間歇性,不適合納入固定電價、剛性供需的電力計劃系統。於是,從「能否賣出去」變成了新能源行業生死線。
根據2025年起施行的新規,全國所有新增新能源發電項目將 全面取消固定電價補貼, 必須參與市場化交易,包括:
-
中長期合同交易: 類似「預售電」,發電企業與用電企業直接籤約,鎖定一定時間段、價格和電量;
-
現貨市場交易: 根據實時電力供需波動,電價可能每15分鐘變動一次;
-
輔助服務市場: 提供調頻、調壓、備用等電網穩定性服務;
-
綠色電力交易: 用戶自願購買綠色電力,附帶綠色電力證書(GEC);
-
碳市場交易: 發電企業可因減少碳排放獲得額外收益。
目前全國已設立多個電力交易中心,如北京、廣州、杭州、西安等地的 電力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統一負責市場撮合、電量確認、電價結算等。
我們來看一個典型現貨市場的示例:
在2024年夏季高溫時期, 廣東電力現貨市場 出現極端波動,谷段電價低至0.12元/kWh,峰段最高達到1.21元/kWh。在這種機制下,新能源項目如果能夠靈活調度(如配備儲能),可以「低價存電,高價賣電」,獲取巨額價差收益。
相比之下,仍依賴中長期合同但缺乏調峰能力的項目,只能以每度0.3-0.4元左右的價格出售電力,甚至在部分棄電時段被迫零價上網。
於是,越來越多新能源企業開始投資 配套儲能 ,一方面用於電網調度響應,另一方面用於價格套利。
除了電價收入,新能源企業還有幾項可能的收入來源:
1. 綠色電力證書(GEC)交易。 2024年江蘇、廣東、北京等省市已啟動GEC交易平臺,用戶(特別是大型工業企業)出於碳披露、綠色採購等目的購買GEC。根據能源研究會數據,2024年GEC成交價區間為每MWh 80-130元,折合約0.08-0.13元/kWh,是傳統電價的一大補充。
2. 碳市場交易。 如果新能源項目用於替代煤電,並被納入全國碳排放交易系統,則可以獲得「碳資產」收益。截至2024年底,全國碳市場價格約為70元/噸CO₂,每度綠電約減排0.8-1.2千克,理論收益在0.05元/kWh左右。
3. 峰谷電價調節與需求響應激勵。 發電企業與高耗能用戶籤訂用電調節協議,在高峰期減少負荷或向電網反送電力,可獲得額外補貼。該機制在山東、浙江、廣東等地試點中推進較快。
在這種機制下,新能源項目的盈利能力不再取決於「我能發多少電」,而是:
-
我能不能賣到好價錢?
-
我有沒有長期買家?
-
我能不能削峰填谷?
-
我有沒有儲能或其他調節能力?
-
我有沒有可交易的綠色資產?
過去那種「搶指標、靠補貼」的項目模型已經走到盡頭,未來新能源企業必須具備金融思維、市場操作能力,甚至要像做衍生品一樣精細管理電力資產。
一句話總結便是: 新能源的「賣電」環節已經不是簡單的買賣關係,而是一場以電為媒介、與政策、市場、碳權、金融協同博弈的系統工程。
為什麼會有棄電?
對於發電項目而言,最大的風險從來不是電站建得成不成,而是「建成之後賣不出去」。而「棄電」就是這個環節中最沉默卻最致命的敵人。
所謂「棄電」,並不是你不發電,而是你發出來的電沒有用戶、沒有通道、沒有調度餘地,於是只能眼睜睜地白白浪費。對一家風電或光伏企業而言,棄電不僅意味著收益直接損失,還可能連帶影響補貼申請、電量核算、綠證生成,甚至影響後續的銀行評級和資產重估。
根據國家能源局西北監管局的統計,2020年新疆的風電棄電率一度高達16.2%,甘肅、青海等地的光伏項目也出現了20%以上的棄電率。雖然在2024年底,這一數據已分別降至2.9%和2.6%,但在某些區域和時段,棄電依舊是項目方躲不開的現實——特別是在中午高光照、低負荷的典型場景下,光伏電大量被調度系統「壓單」,等於發了也白髮。
很多人會以為棄電是因為「用電不夠」,但本質上它是一種系統調度失衡的結果。
首先是物理瓶頸:在部分資源集中區,變電站容量早已飽和,電網接入成了最大限制,項目批得下來卻上不了網。其次是調度機制僵化。中國目前仍以火電機組的穩定性作為調度核心,新能源出力的不確定性讓調度單位習慣性「限制接入」,以避免系統波動。再加上跨省之間的消納協調遲滯,導致很多電雖然理論上「有人要」,但在行政流程和省際通道上「送不出去」,最終只能棄之不用。而市場層面則是另一套滯後的規則系統:現貨電力市場還處於初級階段,輔助服務機制、價格信號體系都遠未完善,儲能調節、需求響應機制在多數省份尚未形成規模。
政策層面其實並非沒有回應。
從2021年起,國家能源局已將「新能源消納能力評估」納入項目審批前置,要求地方政府明確本地「可承載指標」,且在「十四五」多項政策中提出要推動源網荷儲一體化、建設本地負荷中心、完善現貨市場交易機制、強制配置儲能系統以削峰填谷。同時,多地政府出臺「最低消納比例」責任制,明確新能源併網項目年均利用小時數不得低於國家基準線,倒逼項目方提前考慮調節手段。這些措施雖方向正確,但執行進度仍存在明顯滯後——在很多新能源裝機狂飆的城市,電網改造滯後、儲能配建遲緩、區域調度權屬不清等問題依然普遍,制度推動和市場配合的節奏仍不匹配。
更重要的是,棄電背後不是簡單的「經濟低效」,而是一場資源空間和制度結構的衝突。西北的電力資源豐富,但其開發價值依賴於跨省、跨區的電網輸送和調度體系,而中國目前的行政區劃與市場邊界是高度割裂的。這就導致大量「技術上可用」的電力在制度上無處安放,成為一種被動冗餘。
中國的電,為什麼不能用於加密貨幣挖礦?
在大量「技術上可用、制度上無處安放」的電力被閒置的同時,一個原本被邊緣化的用電場景—— 加密貨幣挖礦 ,在過去幾年不斷以地下化、遊擊式的形式出現,又在某些區域重新獲得「結構性被需要」的現實位置。
這並非偶然,而是某種結構縫隙的自然產物。加密貨幣挖礦作為一種高耗電、低持續幹擾度的即時算力行為,其運作邏輯與棄風棄光的發電項目天然兼容。礦場不需要穩定的調度保障,不要求電網併網,甚至可以主動配合調度削峰填谷。更重要的是, 它能把沒人要的電,在市場之外轉化為鏈上資產,從而形成一種「冗餘變現」的通路。
從純技術角度看,這是對能源效率的一種提升;但從政策角度看,它始終處於一種尷尬位置。
中國內地政府在2021年叫停挖礦,核心考量並非電力本身,而是其背後的 金融風險與產業導向問題。 前者關乎加密資產路徑的不透明,容易引發非法集資、跨境套利等監管難題;後者則涉及「高能耗低產出」的產業評價,不符合當前節能降碳的戰略主旋律。
換句話說, 挖礦是不是「合理負荷」,並不取決於它是否消納了電力冗餘,而取決於它是否被納入了政策語境的「可接受結構」。 如果仍以不透明、不合規、不可控的方式存在,那它就只能被歸為「灰色負荷」;但若能夠限定區域、限定電源、限定電價、限定鏈上用途,在合規框架內被設計為一種特殊的能源出口機制,它也未必不能成為政策的一部分。
這種再設計,並不是沒有先例。國際上,哈薩克斯坦、伊朗、喬治亞等國早已將「算力型負荷」納入電力平衡體系,甚至以「電力換穩定幣」的方式,引導礦場為國家帶來USDT或USDC等數字資產,作為替代外匯儲備的來源。在這些國家的能源結構中,挖礦被重新定義為「戰略級可調負荷」,既服務電網調節,也服務貨幣體系重構。
而中國,雖不可能效仿這種激進方式,但是否可以局部、限量、條件性地恢復礦場存在權?特別是在棄電壓力持續、綠色電力短期無法完全市場化的階段,把礦場作為能源消納的過渡機制、把比特幣視作鏈上資產儲備進行封閉式調配,或許比一刀切清退更貼近現實,也更能服務國家長期的數字資產戰略。
這不僅是對挖礦的重新評價,更是對「電的價值邊界」的重新定義。
在傳統體系中,電的價值取決於誰買、怎麼買;而在鏈上世界,電的價值可能直接對應一段算力、一種資產、一條參與全球市場的路徑。在國家逐步構建AI算力基礎設施、推進東數西算工程、建設數字人民幣體系的同時,是否也該在政策圖紙上,為一種「鏈上能源變現機制」留出技術中性、合規可控的通道?
比特幣挖礦或許是中國第一次在「沒有中間人」的狀態下,把能源轉換為數字資產的實踐場景——這個問題敏感、複雜、但又無法迴避。
結語:電力的歸屬,是一場現實的選擇題
中國的電力體系並不落後。風能鋪滿戈壁,陽光灑滿沙丘,特高壓穿越千裡荒原,把一度電從邊疆送進東部城市的高樓和數據中心。
在數字時代,電早已不只是照明與工業的燃料,它正在成為價值計算的基礎設施,是數據主權的根系,是新金融秩序重新組織時最不可忽視的變量。理解「電」的流向,某種程度上,就是理解制度如何設定資格邊界。一度電的落點,從來不是市場自然決定的,它背後藏著無數次決策。電並不平均,它總要流向被允許的人、被認定的場景、被接納的敘事之中。
比特幣挖礦爭議的核心,從來不在於它耗不耗電,而在於我們是否願意承認它是一種「合理的存在」——一個可以被納入國家能源調度的使用場景。只要不被承認,它就只能在灰色中遊走、在夾縫中運行;但一旦被認定,它就必須被制度性地安放——有邊界,有條件,有解釋權,有監管口徑。
這不是關於一個行業的鬆綁或封鎖,而是一套系統對「非常規負荷」的態度問題。
而我們,正站在這條分岔口上,注視著這場選擇正在悄然發生。
參考資料
[1] 中國政府網,《2024年全國電力工業統計數據》,2025年1月。
[2] IEA,《Renewables 2024 Global Report》,2025年1月。
[3] 國家能源局,《2024年度能源運行報告》附錄。
[4] 國家發展改革委能源所,《「沙戈荒」風光基地建設進展》,2024年12月。
[5] 國家發改委,《可再生能源發電項目管理暫行辦法》,2023年。
[6] 路透社,《中國UHV輸電系統評估報告》,2025年5月。
[7] Infolink Group,《中國新能源取消固定電價補貼解析》,2025年3月。
[8] 國家電力調度中心,《華北電力現貨市場運行通報(2024)》。
[9] REDex Insight,《中國統一電力市場路線圖》,2024年12月。
[10] 中國電力企業聯合會,《2024年度電力行業報告》附表。
[11] 國家能源局西北監管局,《西北棄風棄光情況通報》,2024年12月。
[12] 能源研究會,《綠色電力證書交易試點觀察報告》,2025年1月。
[13] CoinDesk,《哈薩克斯坦挖礦政策調整分析》,2023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