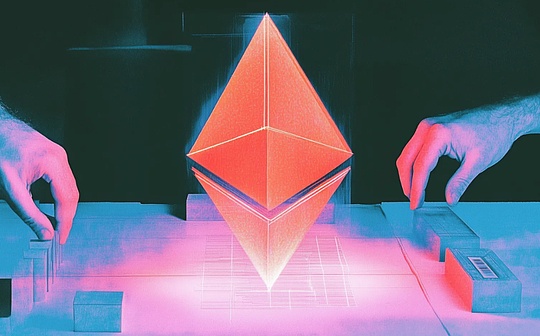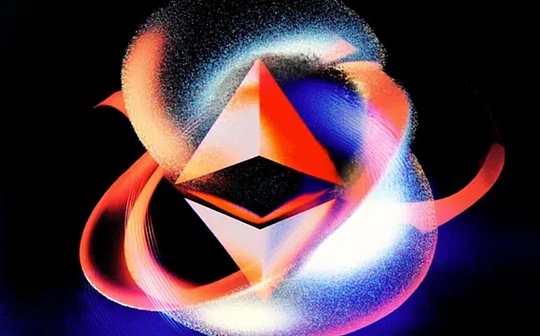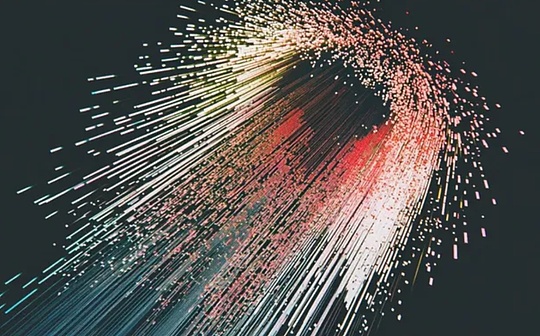作者:Lane Rettig,以太坊前核心开发者、以太坊基金会前员工;翻译:比特链视界xiaozou
几周后以太坊将迎来十周年。然而该项目和社区仍存在内部割裂、发展方向分歧的问题,在日益激烈的竞争中挣扎。上周我写了 以太坊陷入困境的三大症结 ,以及为何因此市场情绪跌至我见过的最低点。上周所述的原因主要与文化相关。本文继续带来三个更务实的原因:人才危机、用户体验割裂以及治理问题。
1、人才危机
如上篇文章所述,我在2017至2019年间以不同身份任职于以太坊基金会。我职业生涯中参与过多个运作失调的组织,在这个由才华横溢但自闭的建造者主导的行业里,早期项目似乎难免如此。即便以这些低标准衡量,以太坊基金会仍是我参与过最混乱的组织(下文详述),这种混乱导致其在吸引和留存人才方面存在严重问题。
人才通常青睐任人唯贤的环境,他们知道努力工作和优秀表现会获得回报与晋升。而我在以太坊基金会看到的恰恰相反:这里存在严重的人才排斥现象。不幸的是,这也反映了整个以太坊生态的现状。以太坊的成功并非源于良好的人才吸引或留存机制,而是在极度畸形的人才管道中侥幸存活。它确实做得不好。
我在基金会的个人经历就是典型案例,也是以太坊生态人才问题的缩影。据我观察,基金会掌权者大多不应该成为掌权者。他们并非因才能被聘用或提拔,相反,他们是Vitalik的朋友、受Vitalik信任的各类特殊关系者,甚至不乏道貌岸然者。虽然基金会多数成员善良勤奋,但有些人人品堪忧,甚至相当堕落且权力欲旺盛。
这种选拔机制存在双重问题:首先无法选出强有力领导者,其次会打击其他成员的士气。它明确传递出这样的信号:在基金会或以太坊生态,成功不靠努力或能力,而是靠天时地利,靠巴结Vitalik等决策者并模仿其价值观行为。我看到那些受Vitalik”庇佑”的人享有财富特权却几乎无需担责,而处境不佳者(包括努力工作的人)永远无法出头。
我不想过多谈论个人经历,但我眼中的基金会极度混乱:领导层不清楚下属人数、博士级贡献者时薪仅25美元、员工薪资常被拖欠、派系斗争与权谋算计横行。我因直言所见所闻树敌众多。
我认识许多离开基金会/以太坊生态的顶尖人才,原因相似;也见过试图加入却遭拒绝的能人。有人遭遇类似基金会的体制问题;有人找不到运作良好的以太坊项目最终另谋高就;有人因报酬不公转投他处;还有人被混乱缓慢的进度劝退。
典型案例不胜枚举。我认为最佳案例是NEAR和Monad等以太坊”衍生”项目。为何这些项目会存在?为何那些才华横溢的创始人不去建设以太坊而选择另起炉灶?为何投资人不注资以太坊而投向竞品?
Web2经济的运作方式值得参考:想开发更好搜索引擎的建造者有两个选择——加入谷歌(若能力出众将获丰厚报酬)或创立公司(可能被谷歌收购)。无论哪种,建造者都获回报,创新最终融入谷歌生态。
以太坊两种能力都不具备:基金会等组织无法为底层贡献者提供包含股权对等的优厚待遇;并购几乎不存在。简言之,经济模型已坏:以太坊无法补偿在底层冒险创新的创始人。基金会研发人员的薪资远低于自立门户或加入竞品。面对批评,基金会总辩称其品牌光环足以弥补风险报酬的缺失。
即便社区支持吸引NEAR/Monad类建设者(他们提前数年实现并改进了以太坊路线图),也缺乏实现机制:既无资金库也无执行主体。因此最具野心的建设者被迫成为竞争对手——即便他们本不愿如此。
这对以太坊的伤害怎么强调都不为过。NEAR在以太坊未能时实现了分片等Eth2.0原始路线图,本可作为Eth2.0发布。如今Monad正重现这一幕——它已领先以太坊整整两代技术,本可作为Eth3.0。虽然NEAR/Monad的去中心化程度不及以太坊主网,但远超现有Rollup,支持更高吞吐量,是更优秀的扩容方案(后文详述)。想象以太坊若能跟上而非落后于这些项目,既有趣又悲哀——这深刻揭示了其经济与治理的问题。
需要澄清的是:当前仍有大量人才在为以太坊奋斗,我并非否定这点。以太坊在人才储备上仍占优,但需关注变化速率而非现状。其人才优势正在萎缩,我认为难以持续。仅靠惯性已不够。”以太坊研发”的光环确实存在(或存在过),但本文所述原因正使其逐渐暗淡。
在当前的生态状态下,人才仍是零和博弈——以太坊的流失就是竞品的收获。我目睹大量人才外流:许多能人已转投他处,留下者也多感沮丧正考虑离开。若想保持竞争力,以太坊必须彻底重构人才管道。如今人才为何要加入以太坊?当别处待遇更优时为何留下?
本文所述问题中,人才危机是我对以太坊未来最大的担忧。任何成功创始人都明白人才是项目命脉。区块链生态一旦出现人才流失便难逆转。以太坊目前仍是行业领袖,但正如我们屡见不鲜的——即便成功的区块链生态也可能突然衰落。以太坊应竭尽全力避免这种命运。
如果具备更成熟的治理体系和人才激励制度——即成功初创企业为保持竞争力所做的基本功——以太坊本可早就解决这个问题了。
2、用户体验割裂
在上篇文章里我简要提及了以太坊的可用性问题,特别是在其沉迷研究和追求意识形态纯洁性而忽视实用性的背景之下。虽然以太坊始终存在(且仍然存在)诸多可用性缺陷——密钥管理、最终确认时间、冷启动问题——但在我看来,最严重的问题莫过于复杂Rollup生态导致的割裂体验。
回想20年前的旅行体验:抵达异国后几乎寸步难行。手机无法使用(并非如今安装当地eSIM就能解决),因缺乏全球漫游标准,你需要在不同地区配备不同制式手机。信用卡失效且无感应支付,必须拿着旅行支票去本地银行兑换当地货币才能消费。当然也没有翻译软件或地图应用,所有事都需用原始低效方式完成。
这正是当前以太坊(若将整个Rollup生态视为整体)的交易体验写照。你需要管理分散在多个钱包的数十个账户,每个钱包都有独特的设计缺陷且均非易用之选。每条Rollup和L2链都有专属Gas代币,令人难以厘清。即便使用ETH作为Gas,相同地址在不同链间转移ETH也非易事。即使对专家而言,记住”哪个钱包的哪条链上有哪些应用的哪些账户”也令人抓狂且极易出错。
更糟的是跨链桥堪称灾难:不可靠、不安全、高手续费且耗时漫长(是否很像旅行支票?)。实际上多数人被迫使用Coinbase或Binance等中心化交易所作为事实跨链桥。这听起来既糟糕又中心化——但别忘了不仅跨链桥中心化,Rollup本身也由小型”安全委员会”(本质是好友团体)集中控制,他们能像交易所般随时关停链或审查交易。这完全违背加密货币的核心理念。
情况还在恶化。各链之间缺乏无缝传输数据/资产的途径,导致流动性极度割裂。若要设计可用的可扩展系统,最愚蠢的做法莫过于在每个分片部署完全相同却无法互通的应用程序——而这正是以太坊现状:Aave和Uniswap等项目被部署在数十条链上,流动性、用户和数据被割裂得支离破碎。这种体验根本不可能吸引新用户入场。
这种局面本可避免。我们总把这些用户体验问题视为理所当然,总把抱怨者当作”不懂区块链原理的笨蛋”打发掉——这种傲慢是错误的,因为责任在我们。这些问题既非必然也非绝症,而是我们主动选择的设计决策。我们本可以不走这条路,现在也仍有转圜余地。
以太坊选择这条歧路有自己的原因:用懒惰方式扩展基础层。早在2017年就已明确,以太坊基础层永远无法满足交易需求。原计划是将基础层分片为数十/数百个相同分片,使账户交易能异步跨分片进行。NEAR完善的分片设计已验证这种方案的可行性——绝大多数复杂性可对用户甚至开发者隐藏,用户根本无需知晓账户所在分片。分片绝非新概念,所有成熟可扩展系统(包括Web服务器和数据库)早已采用类似方案多年。
但以太坊选择了懒惰方案:仅执行Eth2.0路线图前两个阶段就放弃分片,转而让他人通过部署异构L2链(Rollup)自行扩展。这就是”以太坊之道”:选择最开放去中心化(即最不需集中协调或愿景规划)的方案,其余交给市场。
几年后市场给出了答案:涌现出数十上百个竞争链和标准,几乎每天都有新项目诞生。被割裂的不只是用户、应用和流动性,还有社区注意力。大量知名L2项目争夺关注度而非共建统一愿景,缺乏全局互操作标准导致前文所述的UX灾难。以太坊基金会和路线图制定者本应设立基本规则标准,却未能履职。
以太坊拥护者常批评Solana等高吞吐链,称唯有模块化(而非盲目提升单节点吞吐量)才能实现扩展。他们说得对,但现有方案绝非正解。
以太坊社区刚开始意识到问题严重性,但多数人仍在逃避现实。当我指出乱象时,最常听到的回应是:”别担心,某互操作性项目即将问世并彻底解决问题。”这种承诺我已听了多年,却未见任何可信项目能实质性改善UX(而非引入更复杂的中心化风险)。我见过太多失败尝试,深知问题根植于更底层。除非抛弃当前错误的扩展模型转向更合理设计,否则以太坊将丧失竞争力。
目前最佳的互操作方案是NEAR的Intents系统,允许通过单一账户控制多链资产。待其成熟后,或能通过自动调节流动性缓解割裂问题。但Intents旨在实现比特币-以太坊-Solana-NEAR等异质生态互操作,无法单独修复EVM生态的内部问题。
唯一合理出路是回归分片理念。这个想法正随着”原生基础Rollup”(本质类似分片)等提案逐渐兴起。我不确定以太坊生态能否协调出真正解决方案(这需要强有力领导力和深度变革),但绝对值得尝试。
3、治理问题
前文已提及以太坊基金会(EF)的部分运作失调现象,至少是我几年前亲历的状况。虽然不清楚基金会的当前情况,但我不断从朋友熟人处听闻类似的混乱故事。
上述问题实为更深层顽疾的表征。当一个组织无法留住人才、无法公平补偿贡献者、且错误人选被提拔至权力岗位时,这预示着系统性病症。对以太坊基金会而言,核心症结之一在于治理结构。正如Vitalik近期承认的,他始终实质掌控着基金会——尽管基金会设有三名董事会成员,但Vitalik拥有三票表决权,形成事实上的独裁控制。若此情况有变,也未见公开声明。
基金会的根本问题在于缺乏问责机制。Vitalik无需对董事会负责,又因非营利性质,不存在可介入纠错的股东(即便情况已如此糟糕)。与传统非营利机构不同,基金会及其董事会甚至无需对捐赠者负责。Vitalik固然是卓越的技术领袖,但问题不在于个人能力——任何缺乏透明度和问责制的组织都注定失灵。
在这种缺乏监督的环境下,权力往往流向野心家手中,这正是我在以太坊基金会亲眼所见的。这种状况对任何组织都属灾难,对于身处”构建公平透明人类系统”的加密生态核心的以太坊基金会更是双重讽刺。这种虚伪正是我离开以太坊的主要原因——它令我夜不能寐。
以太坊基金会初创时期曾有过强势领导者Ming Chan,但她作风强硬树敌众多。最终Vitalik等决策者因难以掌控她而终止合作。我在职期间,目睹多位独立敢言的负责人因此类原因遭解雇。
继任执行董事Aya与Ming截然相反:过去七年力求维稳,但绝非变革者。面对激烈批评,基金会近期才仓促推行双执行董事制,任命Tomasz Stańczak与Hsiao-wei Wang联合领导。尽管二人品行端正且怀有改革诚意,但我怀疑这种架构能否带来实质改变:Hsiao-wei本是研究者而非官僚机构领导者(这正是基金会陷入现状的主因);Tomasz若有充分授权或能推动改革,但直觉告诉我他难以获得实施艰难变革的许可。以太坊基金会很可能继续蹒跚前行,长久成为以太坊生态的负面标杆。
这本可避免。以太坊基金会成立之初的计划是在生态成熟后解散——多位基金会创立参与者向我证实,它本应只是短期助推器。基金会在早期确实关键,但如今它更像是阻碍而非催化剂。解散基金会将为更多团队创造承担责任的空间。
你或许疑惑:为何不绕过基金会推进事务?事实上已有数十个资金充沛的组织在独立推动以太坊研发和社区建设。但问题在于:基金会尽管缺陷明显,其庞大的资源和权威仍使其在路线图制定上难以被挑战;同时这些组织多为营利公司,各自为政的愿景恰是生态割裂的根源。以太坊这类公共物品项目至少需要类似Linux基金会、W3C等具备公信力的中立协调实体来制定标准——这些组织虽不完美,但至少设有问责机制。
若以太坊生态欲重振雄风,必须开始探索绕开以太坊基金会的协作路径。近年来以太坊的发展成就源于基层努力,而非基金会的领导。Etherealize等新兴组织的出现标志着这种尝试的萌芽,但恐怕为时已晚。问题的复杂性在于:以太坊社区始终未能就基金会问题展开诚实讨论,这种沉默本身已昭示着更深层的危机。除非发生改变,否则以太坊将持续挣扎前行。
(注:本文观点仅为作者个人观点)